放大资金,增加盈利可能
配资是一种为投资者提供杠杆资金的金融服务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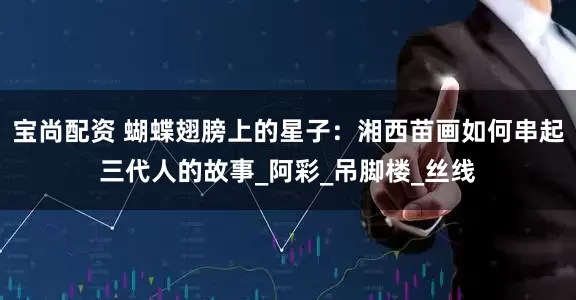
湘西的晨雾刚漫过吊脚楼的木栏,阿彩的绣花针就已经在靛蓝土布上跳舞了。她指尖缠着的五彩丝线,像从屋后酉水河捞起的朝霞,一针下去,布面上就长出只振翅的蝴蝶。婆婆总说这丫头的手是被苗王点过的,要不然怎么能把山间的花鸟虫草,都绣得像是下一秒就要从布上跳下来。
阿彩的绣绷子是祖父传下来的老物件,红木边框被几代人摩挲得发亮。她七岁那年蹲在火塘边,看祖母给新嫁娘绣嫁衣,那些盘旋的龙纹在炭火映照下像是活了过来,从此她就攥着母亲的衣角,非要学这门手艺不可。母亲拗不过她,把陪嫁时带的丝线匣子打开,教她认那些靛蓝是用板蓝根泡的,绯红要掺朱砂,明黄得采来栀子果反复熬煮。
那时寨子里的老人们总坐在大青树下晒太阳,看阿彩趴在石桌上描花样。她画的苗族姑娘裙摆总比别人的宽,说是能兜住更多阳光;画的锦鸡尾巴要拖到画面外头,说这样才显得要飞进云端。有回她给自家吊脚楼的廊柱画缠枝纹,故意在藤蔓尽头加了朵从没见过的白花,被祖父用烟杆敲了手背:"祖宗传下来的纹样,哪能说改就改?" 阿彩委屈地抿着嘴,却还是趁祖父不注意,把那朵花描得更鲜亮了。
十七岁那年的四月八,阿彩穿着自己绣的百鸟裙去赶歌会。裙摆上的凤凰翅膀用金线锁了边,走起来簌簌作响,像是有无数雀鸟在振翅。寨子里的后生们吹着芦笙围过来,她却只顾着看邻村老阿婆背篓上的鱼纹 —— 那些波浪线画得比河水还要灵动。老阿婆笑着说这是年轻时跟货郎学的,货郎见过洞庭湖的大鱼。阿彩当即把裙角的锦鸡改成了腾跃的鱼,惹得母亲直叹气:"哪有姑娘家把鱼绣在嫁衣上的?"
展开剩余62%秋收后的鼓藏节,阿彩被推去画祭堂的幡旗。族老们指定要画《蝴蝶妈妈》的古老传说,她却在蝴蝶翅膀上绣了圈细小的星子。"天上的星星落在翅膀上,才显得蝴蝶妈妈能带来光明。" 她仰着头跟族老解释,手指飞快地把银线嵌进布纹里。祭祀那天,幡旗在风里舒展,阳光照过银线时,真的在地上映出星星点点的光斑,族老们捋着胡须笑了,说这丫头的心思比酉水河的漩涡还多。
二十岁那年,省里来的画师住进了寨子里。阿彩背着丝线匣子去看他作画,见他把吊脚楼画在宣纸上,却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"画师先生,您的屋檐下该画串玉米。" 她蹲在画架旁,用炭笔在屋檐角添了几笔,"还要有只啄米的鸡,这样房子才像有人住。" 画师眼睛一亮,非要跟她学绣布上的纹样。阿彩教他用十字针脚表现梯田的层次,他教阿彩用透视法画层层叠叠的山峦,两个人在晒谷场上画了整整一个秋天。
后来阿彩的儿子满月,她给孩子缝百家被,把寨子里老人们教的纹样都拼了上去:东边阿婆的石榴纹,西边大叔的耕牛图,还有画师先生教她画的远山。最特别的是被角那朵她七岁时画的白花,如今旁边多了只衔着丝线的小鸟。婆婆抱着襁褓笑得眼角起了褶:"这鸟儿是要把咱们的手艺衔到更远的地方去呢。"
去年开春,阿彩带着学生们在新盖的文化站墙上画画。十六岁的苗族姑娘阿依学着她当年的样子,非要在传统的龙凤纹里加些几何图案:"老师,外面来的游客喜欢看新鲜的。" 阿彩没像当年祖父那样敲她的手,反而帮她调了更鲜亮的颜料:"但要记得,几何图形的角得磨圆些,就像咱们吊脚楼的木柱,得顺着山势弯才稳当。"
夕阳西下时,文化站的墙成了幅流动的画:靛蓝的天空下,吊脚楼踩着青石板,酉水河绕着梯田,穿百鸟裙的姑娘们提着竹篮,篮子里盛着的,既有金黄的玉米,也有开着奇异白花的野草。有个背着相机的游客站在画前看了许久,突然问阿彩:"这些画里的故事,能编成书吗?"
阿彩正给学生们示范如何用藤黄调日出的颜色,闻言回头笑了:"不用成书哦。你看 ——" 她指着不远处赶回家的农人,他们肩上的扁担缠着彩绳,竹篓上的漆画还闪着光,"生活着的地方,就是故事在长呢。" 晚风拂过新画的墙面,颜料的气息混着苗家腊肉的香气,远处传来孩子们的笑声,像是从画里流淌出来的音符。 #湘西艺术#
发布于:湖南省信钰证券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